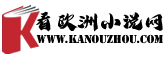赵恒沉吟半晌,明知韩杞所言虽无懈可击,却纯属危言耸听,他作为一国之君,不能和韩杞一般见识。
尽管,契丹大军声势,令他心惊不已,但他仍有自己的底线,地是绝不能割让的。
当下,不冷不热地道:“国书权且留下,关南之争尚需再议。有无和议、再战与否,也须潦草不得。外使到此,总要以礼相待的。待朕聚会诸臣,计议定夺,再回复不迟。”
韩杞细细揣摩赵恒之言,虽看是强硬无比,在土地上毫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最后一句,却留下了令人遐想的无限话头,他似乎明白赵恒有所坚定、有所舍弃的底线。
当下,再也不说实质性的话题了,话锋一转,大谈契丹向慕中原文化和繁荣,如两国盟好将是天下生民之幸的扯淡话,而后在一片宾主融洽中,随曹利用退了下去。
赵恒目光复杂地看着韩杞的背影,真个心潮澎湃、难以平息。
退一步说,他力排众议、一力主持能与契丹人达成和议,世结盟好,尽管会有损自己声望,却也须不负前辈“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为惧”的遗训。
征签天下丁壮在河朔你来我往的征战,真的不如以和为贵,纵然不是为生民着想、也是令自己省下了许多的烦心事,哪怕多给对方些金帛也行,总比动辄数百万贯、上千万的军费合算许多。
王璇自然也在众臣的行列中,尽管他没有资格说话,但自始自终他没有笑一笑,脸上始终包裹着一层冰冷的寒霜,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赵恒面对沉默的众位大臣,也不知该说什么为好,他暂时还摸不准臣下的想法,但他相信对苦于边患的文臣来说,能够花去少量的钱财换个平安,从某种程度上还是能够接受的。
当然,寇准等坚决主战的大臣必然要反对,这也在情理之中,他逐渐把这种想法稳固下来。
暗自决心,无论花费多大的代价,也要平息了北方的边患,契丹所展示的强大力量,绝不是大宋所能战胜。
一旦陷入旷日长久的战争,对赵家并无半点好处,得利的只能是武人,且他一直谋划用文人,逐渐消弱行营都部署制度,战争不真正结束,却无法实施,至少他如此认为。
武人尚有三大支撑,他必需要拿下来,才能放心赵家后代传承江山。将门世家已逐渐凋零,不断被潜邸将帅所取代;彻底架空禁军厢一级都校,甚至打乱军编制,实际控制权逐步过渡到常驻兵马都监制,也就是说由守臣率兵;行营都部署为武人之最,权力极大,他并不放心,哪怕都部署由潜邸将帅担任。’
向敏中出镇陕西,安抚十余军州,所受权力与都部署毫无区别,是他刻意为之,是以文人取代都部署的尝试。
“来而不往非礼也,契丹有意和天朝和好,诸位卿家意下如何?”
众人在皇帝的感慨之言下,谁也不愿意先说话,毕竟是关乎国体的事情,谁也不愿在强横的寇准面前做露头鸟,使自己成为攻憾的对象。
赵恒见众人都缄默不语,心下颇有不予,朝廷优待士大夫,这些人关键时刻却明显的缩头缩脚,想想真是可恨之极,他的脸色逐渐沉了下来。
此时,王璇心下正激烈的斗争,南北和解、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不断冲击他的思想,他已不相信自己能说服赵恒。
“陛下。”冯拯无视寇准凌厉的目光,高声道:“既然契丹有诚意,除去关南三州之外,为河北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谋划,似乎还是恰当的,还望陛下圣裁。”
“冯大人此言差矣。”冯拯话声刚刚落地,寇准毫不客气地瞪了冯拯一眼,口气极为不悦。
当众人目光转向寇准时,他那双精光闪烁的眸子,紧紧地盯着冯拯,缓慢而又尖刻地道:“不知冯大人有何良策安邦定国,还河北生民休养生息?难不成年年送出生民膏粱,这又是哪门子安邦定国之策?”
冯拯那张白净的脸涨的透红,胡须也微微颤抖。
对于寇准的指责他更无法反击,毕竟很多人都承认军事形势有利,歼灭契丹人的论调在大臣中很有市场,用钱买平安,无论怎样说都很难堪。
王璇暗自松了口气,寇准算是说出他的心里话。
“陛下。”寇准斥责完冯拯之后,目光直视前方,面沉如水、似乎在等待赵恒的决断。
赵恒内心深处也非常为难,他没有必胜信心继续打下去,又怕武人掌兵太久,议和的政治代价太高,太没面子了,孰轻孰重,久久不能决断。
大殿里的气氛,异常沉闷之际,周怀政匆匆入内,在看了看殿内的众位大臣之后,把一份金字牌塘报呈给了赵恒,道:“陛下,刚刚到的保州官塘捷报。”
赵恒折开塘文,匆匆御览之后,脸上闪过一抹兴奋地喜悦,继而又是静若止水的沉寂。道:“寇卿看看吧!”
寇准细细看过周怀政递来官塘,未待赵恒言语,便抚掌大笑,道:“壮哉、壮哉,这一仗杨延昭打的算是可圈可点,看来缘边诸将果不负陛下重望,把战火扫到契丹境内,臣倒想看看契丹还有什么办法,能阻挡诸位大将的铁骑。”
赵恒轻轻摇了摇头,脸色不予地道:“若是全力围剿契丹,到时恐怕非战不可了,那契丹孤注一掷,置之死地而后生,胜负终属难料,还是围三厥一为好。”
寇准听出赵恒背后的意思,只要不割地求和,许上些金钱,放弃歼灭契丹军主力的机会,也在所不惜。
当下,非常不满地道:“陛下所虑,臣亦是想过,如今契丹精锐久困城下。待他士气稍懈,便可挥师反攻,把契丹人打出河北。断没想到要在定、瀛各州断其归路,迫其弃甲抛戈。倒是杨延昭在塘文中说的有理:我朝守土而战、士气易盛,契丹人孤军深入,虽暂时围了澶州,又何尝不在大军重围之中?只要各路大军密切配合,契丹不过是待宰鸡犬。不久军心必乱,斗志瓦解,数十万精锐有何作为?不投降又该怎样!而今逼降萧绰,非但幽蓟诸地唾手可得,就是恢复汉唐故土,又能有何难!”
赵恒并不认为寇准说的有多少道理,何况在汴京时,王璇早就有议论。
他只是摇头道:“虽说河朔局势稍有缓解,但契丹人实力犹在。便是侥幸胜了,又要伤亡多少军民?朕心实不忍生民涂炭。还是尽快和契丹人达成盟约,各守南北,多许些金帛也未为不可,只要不是祸国殃民便可。”
一直没有说话的杨亿,在寇准的默许的目光下,朗声道:“陛下,臣以为契丹狼子贼心,南北议和总不是长久之计。而今陛下御驾亲征,天子生民气壮、内外士气正盛,河北各州频频有捷报,契丹退路几乎被王超、杨延昭等断绝,斗志必丧过半,趁此良时与其决战,必攻无不克,何苦给后代子孙留下万千隐患。”
“此举国之战胜负暂且不论,空耗国帑,伤及生民,只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焦土,怕要失却人心,那时又对得起谁来?朕只不想乘人之危,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诸位卿家就不要再说了。”赵恒深深叹了口气,不再言语。
王璇淡然一笑,赵恒的话中充满了逻辑上的矛盾,甚至说是非常荒唐的逻辑,但真的是不想打了。
金帛从哪里来呢?只能从黎民百姓身上得来的,这场空前的大战是要消耗巨大的国帑,使得很多百姓流离失所。若是和议,就需要几十年、上百年都消耗国帑、殃及生民,每年消耗在边地的防务费用一点也不能少。
说话权永远在武力强大的一方,即便是有一个长久的和平,但你必须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应付随时可能突发而至的战争,孰重孰轻焉不昭然若揭!
他暗暗叹了口气,把念头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他需要好好地考虑下一步。
寇准眼看赵恒面色难堪,显然把议和的主张定了下来,、且渐渐对坚决抗战的言论有了不满意。
他也不好再戗火,便道:“结盟议和非为不可,当初汉赐玉帛于单于,也是挟大胜恩加赏赐安抚,令其敬而畏之,且止一次。唯我朝这般赏赐累年不绝,前无古人,亦空耗许多国力,实不可取。臣意在于此战必须要大破契丹人,使其献还幽蓟诸地之后再赏些玉帛给他,叫他永不敢生南觑之心、永不敢小觑我朝威仪!”“何况契丹蛮族,尚未开化,劫掠成性,不以武决,难服其志,不战而赐之,知情者乃陛下体恤生灵,不知情者即陛下惧而求和,而无论天下人如何作解,此时议和必骄其志,日后边关难以安宁,孰知今日用兵之功过!”
赵恒哪里听得进去,摇首道:“朕意已决,能用天朝上国仁德成盟,契丹必能心悦诚服。”
寇准愕然片刻,明白再说下去,只能适得其反,不如另想办法。当下道:“陛下,战也罢,和也罢,待臣去问一问契丹使臣,摸摸契丹实意,再来复命不迟。如今北城形势已稳如磐石,还望陛下渡河,在北城接见契丹使臣。”
赵恒见鲠直的寇准竟退让了一步,也不知是喜是忧,要知道寇准是出了名的臭脾气,连太宗皇帝的账也不买,能够令其软下来真是不容易啊!
既然寇准服软,北城已经稳定下来,再去一趟也是应该的,前天夜里匆匆回到南城,实在太没面子了。
寇准在出去后和韩亿两人来见了韩杞,自然先礼后兵,先客套一番再进入正题。
但这位韩杞也是口齿不凡,忠心笃志,强词夺理分毫不落下风,几人你来我往争执许久也未见结果。
寇准心中是那个窝火啊!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猖狂的使节。在韩亿退下后,他憋着一口气,要坚决奏请发兵决战,但杨亿坚决不同意他这么做,并大胆地向他说出外面的谣言。
时下御营内部和南城私下里传言:“身为人臣,可好挟迫主上唯意是策、肆意而为!”
“高高在上,目中无人,失尽了臣子礼数。”
“独断专权,为邀头功全不将主上放在眼里,不怕失了阴德!”
寇准根本就不屑一顾,他不愿不睬这些小人谣言,他认为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这些小人不过是诽谤、中伤别人以图侥幸之功罢了。
王璇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退出去,他却留在赵恒身边。
赵恒似乎很疲乏,他靠在御座上,慢悠悠地道:“如今朝廷多事之秋,实在是经不起举国之战了!”
王璇木着脸,低声道:“陛下,失去这次大好机会,契丹仍旧占据燕山之地利,而我在河北平原上一马平川,还要消耗巨大的军费受制于人,又要多出给契丹的岁赐,恐怕日后要竭尽天下民力了。”
实际上,王璇在尽最后一步努力,他知道大宋诚然是蒸蒸日上,却不能把强硬和妥协有力的结合起来。
再加上开国形势的艰难、太祖皇帝事业未尽过早驾崩,造成了边地无险可守,汴京处于四战之地,造成了天下财力不断供应汴梁,边地驻军消费极大的钱粮。
虽然,大宋拥有最繁华的商业社会和最开放的思想,但政府财政却显得非常拮据,以至于天下财力不足以应付军费开支,导致在更强悍的蛮族打击下,整个帝国土崩瓦解。
赵恒淡淡地道:“卿料事真是精准,但却还是不明白天下大势!”
王璇心中很不以为然,对赵恒所言天下大势很不以为然,暗道赵恒不过是欲盖弥彰而已。
很多年之后,他才在一连串的纷乱内政外事中,真正体会到了赵恒所说的天下大势,冷静下来重新思考这段令人遗憾的历史。
他忽然抬头,目光闪烁,决然道:“既然陛下决心已定,臣请出使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