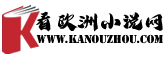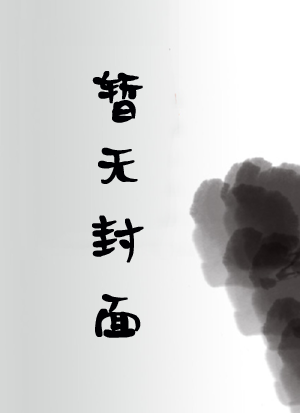§遍地基金会
对促进台湾和大陆进行交流,一个功不可没的组织是一个基金会——“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其董事长是辜振甫。著名的“汪辜会谈”,成了到目前为止海峡两岸最高规格的接触。
台湾各式各样的基金会很多,似乎每一次聚会都能发现几个基金会。有时你不主动去发现,基金会还会撞上你。
在高雄飞香港的班机上,我旁边坐着一位台湾太太,她很自信地断定我是跟书有缘的人,于是主动搭话,谈读书。原来她是“周太太读书基金会”的成员,这个基金会只有七个会员,全是太太。不再扩大,人多了不便活动,不便讲话。每两周聚会一次,每次两个多小时,只谈读书体会,不得谈家长里短、婆婆妈妈。这次聚会要推荐出一本新书,供下一次聚会时讨论,中途有人不喜欢,还可以再推荐新书。这个组织是由一位姓周的太太倡议建立的,并拿出了一点自己的积蓄给大家买书。其实这个读书会花不了多少钱,聚会地点各家轮流,谁做东负责提供茶水就行。
据这位读书基金会的太太讲,在台湾这种自发的小组织很多,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又不坐班的太太们,更喜欢参加这样的读书活动。我问她读不读大陆的书,她说简化字读起来太困难了……
这大概是最小的基金会了,且属于自助自娱的性质。更多的基金会是助人、助事,或纪念某个人、某件事。
台北一富翁,领导着四个性质不同的基金会。其中一个是每月向一个文艺组织资助二十多万元新台币做活动经费,包括给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发六万元的津贴。
一个作家每月需要从一个富人那里领取工资,这说明商品社会有情,还是无情?这种情况极其少见。在商品世界,所有的人都得靠自己,假如你靠写作不能维持生计,就得另谋其他职业。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依靠,可以终生端“铁饭碗”。但每个人活得错不错?至少不比有“铁饭碗”的人在经济上差。商品经济培养人的生存能力,长本事。道是无情也有情。
台湾文艺团体很多,有些文艺家协会、作家协会,从会长到会员都另有职业,他们的关系既松散又紧密。松散的是平时分布在各行各业,互不搭界,各干各的,没有经济、人事、政治上的攀比、竞争和种种矛盾。如果大家要聚在一起,那只为了一个原因:有文学活动。因此,文学的关系,文学的情意,反而更紧密。你如果觉得这种紧密妨碍了你,可以疏远一些,可以不参加一些活动,没人怪你。毫无疑问,五花八门的基金会表达了商品经济有情的一面。其根据是所有的基金会都是为了做好事、做善事而成立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发现一个鼓励作恶学坏的基金会。
既然产生了这么多基金会来做好事,那就说明这个世界很不完美。无以计数的基金会对贫富悬殊的商品社会起到了平衡和保护的作用,它使一些富人变成了善良的好人,甚至是英雄,载入史册。无论他们有多富,是怎样富起来的,今后还会有多富,都被社会承认是道德的事情。一些急需钱的事和人,又很幸运地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就有可能通过基金会得到所需要的钱。让现代人在紧张激烈、冷酷无情的商业竞争中,感受到一点温情、一份真诚。得到帮助的是极个别的事和人,知道有基金会存在的是整个社会,缓解了许多冲突,给商品世界增加了些许情感亮色。
市场经济唯市场的马首是瞻,是“唯利是图”的。基金会则是从文化和道德的角度对此加以调节。
没有人能告诉我,世界或台湾总共有多少基金会?基金会有多少品种?只能就我所知道的分一下类,发现文教方面的基金会最多。这既说明天下的文教行业都比较穷,最需要帮助,又说明经济时代对文化的重视。金钱向文化倾斜,借助文化提高经济的品格,塑造良好的形象,对发展经济大有裨益。办基金会并不完全是赔本的事。根据基金会的多少,其品位和办事的效率如何,大体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
市场经济又可以称为“富人经济”,基金会正是“富人经济”的产物,没有富人的赞助,没有钱,是办不成基金会的。但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愿意办基金会,也不是所有的基金会都名副其实,有些基金会只挂牌子不干事,或干事很少。基金会更不都是赔钱的,有的把基金拿去投资、经营,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现代种种基金会绝不简单地等同于古代舍粥的大锅。它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形形色色的基金会,可以观察当代社会诸多的社会情态和人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