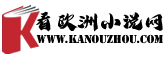第十回 孙可望归降永历皇 吴平西大破刘文秀
张献忠自与李自成分军,先下河南。明将如左良玉、黄得功,先后挫败,张献忠于是乘势入川,取成都为京称帝。人民畏其杀戮,多为从附。及三桂起兵入川时,张献忠已死,遗将孙可望素擅威权,于是代统张献忠之众。未几南京为清帅肃、豫两王所破,史可法已殉难于扬州。福王既死,南明于是亡。明永历帝为明神宗万历之孙,初封桂王,自南都败后,即称帝于肇庆,那时正巡幸安隆。
张献忠遗将孙可望方欲由川入湘,听闻永历帝将至,独上表向永历帝称臣。永历帝一面降旨慰奖,令孙可望以本部安抚四川,然后北讨伐,以图恢复。孙可望得旨大喜,先发出檄文,布告远近。那时人心思明,以为孙可望此举,已悔于前附助张献忠之非,现在已反正,因此纷纷从附。哪知孙可望只是狼子野心,自怕势力不能抗敌建州人马,因此恰值南京福王既败,福州唐王也亡,独有桂王即位于肇庆,改元永历,那时两粤、滇、黔及江西、湖南尚多奉永历,就欲借东明之势力,阳向永历帝称臣,实则欲永历帝遣将分兵牵制大清国人马,自己好于中取事。现在以人心相附,以为有机可乘,便发出一道矫檄。
自这道檄文一出,正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远近人民以为孙可望从此反正,据四川之众与永历帝相合,实不难恢复中原,因此纷来从附,军声复振。那时孙可望以人心既信自己,且又蒙永历奖谕,便欲乘此机会,托迎驾之名,先挟持永历帝至成都,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待平定天下,再图大位不迟。便遣心腹大将王复臣,领兵直出贵州,至陵安迎接永历皇帝。
那永历心上,以四川向称天险,可以久守,便欲随入成都。刚好晋王李定国在旁,力持不可。原来李定国为人久经战阵,性复沉毅,久为明将,多著勋劳。自永历帝继位后,即委定国以兵权。定国此时实以光复自任。忽听孙可望归降,并来迎驾,便向永历帝谏道:“孙可望又名孙朝宗。张献忠因他悍勇,收为义子,所经战事,都以劫掠为事。当献忠破蜀时,尽收府藏金银,载入锦江,致为川将杨展所杀。可望幸逃,于是代领其众。现在以三桂将行入川,于是阳为称臣,实欲与我合而抗敌。此等人狼子野心,不足倚赖,臣以为可利用,则利用之,不宜倚为心腹。设相随入川,一旦或有不测,实非国家之福也。”
永历帝道:“朕以他人马尚多,可为助力,正欲倚之。以朕今日栖息南地,正思北返,若不借资群策群力,事也难济。以四川之雄,孙将军之众,若失此机会,实为可惜。”李定国道:“臣固言可用则利用之。不如封以好爵,使兴兵北讨伐,以牵制敌军。若他派员来迎,只言才行即位,去留为人心所关,待时机稍定,然后入蜀可也。”永历帝从其言,便以冠服赐命,封孙可望为景国公,令其兴兵北讨伐。
王复臣迎驾去后,以永历帝不肯驾幸成都回复可望,可望大不满意,便谓复臣道:“明帝尚疑我也。但我等汗马十数年,李、张二人究无寸地,而清国坐享渔人之利。我等实当归辅明朝,挈天下而还朱家,以雪大耻。若大功既立,不患明帝尚疑我也。”帐下总参谋刘文秀进道:“明公若始终存此心以助明朝,实国家之幸也。北京之师,我当斩三桂之头以献诸麾下。”孙可望大喜,便令刘文秀提兵五万,以王复臣为副帅,往迎三桂,孙可望自统大兵为后援。孙可望既派出刘文秀、王复臣领兵往迎三桂之后,知道两军相持,必费时日,自计待刘、王两将去后,至十五日起兵也不迟。
可望又是个登徒之辈,天天只是迷于酒色。当张献忠亡时,遗下妃嫔十数人,都是张献忠蹂躏各省时掳掠得之者,中多殊色,自献忠亡后,孙可望择其美的据为己有。有名杏娘的,年约二十,通文翰,善歌舞,为叙州生李功良之妻,及张献忠称号而后,即封为贵妃,极加恩宠。献忠既亡,杏娘复归于孙可望。那孙可望既得杏娘,更是朝夕不离,因此自从分发刘文秀、王复臣带兵往迎吴三桂之后,本该从速带兵出发,做刘、王两将的后援,偏是那杏娘撒娇撒痴,孙可望又是依依不舍。
那时前锋已飞报道:“吴三桂人马,大队将到达叙州。”左右属下都请孙可望从速出兵,并道:“自张大王死后,四川已复失。现在将军以百战之劳,复取四川,倘有差池,后日将不可收复。以吴三桂非别将可比,为人悍勇耐战,兵马又多,若前驱稍挫,他将全军拥进,直进成都,那时救援已无及矣。为今之计,速进大兵,既可为刘、王两将的后援,又可以振前敌的军心。军心一振,敌气自夺。若将军犹豫不决,后悔无及矣。”孙可望也以为然,仍再向杏娘说,力言不起兵不得。杏娘偏不肯离孙可望,可望无奈,便带同杏娘一齐出兵。那杏娘向不曾见过战阵,又不曾经过跋涉,因此一路上只是缓缓而行。
那刘文秀、王复臣领兵先到达重庆。这时川省人心虽愤张献忠从前横暴,但孙可望一旦反正,民心自然欢喜。恰清将带兵入川的,又是吴三桂,人人共愤,因此乘孙可望一时反正,也纷纷从附。那刘文秀又善抚士卒,在军中并与军人同甘苦,是以重庆、叙州诸郡县向日所失陷已隶清国版图的,都次第收复。
当吴三桂大兵到时,一来兵行已久,又在疲战之后,苦难得力,怎当得刘文秀人人奋勇。因此吴三桂迎战时,大小数十战无不失利。三桂顾左右属下道:“不料孙可望军中有如此劲旅,不料他部下又有如此能员。本藩自从宁远回京,直至今日,何止百战?无坚不破,无仗不克。现在竟迭遭挫败,将有何面目见人耶?”参谋夏国相道:“大王差矣!以大王自离京以来,部下虽都能征惯战,但年来三军无日不在战阵中,疲瘁极矣。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强而求胜,势难如愿,白白地自取其辱。不如退守保宁,深沟固垒,以复养元气。待敌军有隙可乘,然后乘而尾随之,此万全之策也。”三桂道:“保宁果能久守耶?”夏国相道:“保宁城池虽小,但地居险要,据此可以当敌军之冲。我退而他若来追,是我已反客为主矣。因而破之,不亦易乎?”吴三桂便传令敛兵,退守保宁。
文秀听得,急传令追赶。王复臣劝道:“我军连胜,已足壮人心矣。论人马多寡,我不如彼,若以孤军深入,诚非计之得者。不如待孙帅领兵到时,合而攻之,三桂即一鼓可擒矣。”刘文秀又道:“三桂,虎也。现在敌军既败,若不迫之,将令再养元气,后更难制,自当乘势追之。且吾军所向克捷,部下人马也不为弱,何必待孙帅一军,始行进取耶?”便不听王复臣之言,领军直追击三桂之后,直至保宁,传令分军四面围攻。
王复臣又道:“望将军切勿围城,以三桂虽败,尚未大挫也。困兽犹斗,况他拥十万大兵乎?古人说得好:置诸死地而后生。三桂当困危之际,鼓励三军,也易为其所用也。若不围城,则敌军唯有弃城而遁,我因而收复土地,不也宜乎?”刘文秀不听,只传令围城,并令部将张璧光围西南,文秀围西北,转令王复臣指挥各路。分拨既定,把保宁围得铁桶相似。
那时三桂方亲自巡城,至西南一角,谓左右属下道:“此可袭而破之,不知谁人围此间?”左右属下道:“此张璧光也。向为张献忠骁将,十分悍勇。”三桂道:“吾也听闻其人矣,勇而无备,不足畏也。”乃令精骑突出西南,转战而东,三桂自为内应,以破文秀。吴三桂见张璧光军势懈惰,可以袭破,便定策遣精骑突出西南,转战而东,自己自为内应,准备乘势由东门攻出。
那时王复臣在军中,见保宁城上隐隐旌旗移动,便谓刘文秀道:“三桂将出矣。宜告诫三军,速做准备。”刘文秀道:“兄何以知其将出也?”王复臣道:“三桂退守孤城,非便退也。敌军以十万之众千里而来,方欲踏平成都,安有因小挫折即行退走之理?敌军扎守保宁,实欲窥我军,乘懈再进。弟正为此虑,因此时常留心。昨夜见城楼上各旌旗隐隐移动,非突出掩袭而何?将军当有以防止。”刘文秀道:“足下实属精细。但我们追三桂至此,只欲求战。敌军突出而我迎战,固所愿也。”王复臣道:“我所虑的,只张璧光一军。璧光勇而无谋,性又轻敌,不败何待?此军一败,即震动诸军矣。倘有疏虞,四川震动,不可不慎也。”刘文秀道:“兄言也是。”说罢,正欲传令张璧光军中,忽西南角上喊声大震,保宁城内有数千精骑突城而出,为首一员大将乃胡国柱,直攻张璧光一军。张军都未有准备。那张璧光一来轻敌,二来又不料吴军突至,一时慌乱。张璧光率军混战一会,无心恋战,只望东门而来,欲与刘文秀合军。胡国柱乘势赶来。刘文秀知道张军已败,一面防吴军由东突出,一面欲援应张璧光。
三桂在城上已知胡国柱得胜,吴三桂由东门即率兵杀出,正攻刘文秀一军。刘军以三桂掩出,军心大乱。王复臣一军,又为张璧光所扰,不能成列,欲退兵数十里,暂避吴军,再图进战。刚好事有凑巧,上流山水暴涨,三军更为慌乱。刘文秀、王复臣两军都不能支,三桂即号令诸将乘势合击。王复臣军中多有逃窜,复臣手斩数人,犹不能止。那时被吴军围困数重,复臣大呼道:“你们当见扬州之事,若降,必无生理。如果不奋力,当尽死于此矣。”军士听得,雄心一振。复臣一马当先,手毙吴军十余人,军士都随复臣奋斗,吴军死伤也众。三桂转怯,欲复退入城,夏国相谏道:“若再退,则保宁不守,而三军性命也难保矣。成败在此一举,王爷勿自馁也。”三桂大省悟,复鼓励三军勇进。那时复臣军士已渐渐疲乏,围者又众,自知必败,乃叹道:“恨竖子不听吾言也。大丈夫不能生擒明王,光复祖国,已自羞矣,岂可复为敌所辱?”于是拔剑自刎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