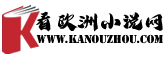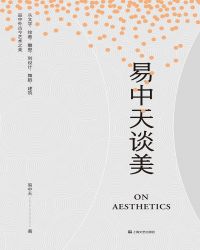CHAPTER 11
论审美的发生
〚一〛前提
李志宏先生《中国当代美学的理论支点:人的本质还是人的智能》(原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11期)对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都进行了批评。学术研究中有不同的意见,原本是十分正常的事情,问题是有没有对话的可能,即论辩的双方有没有大家都同意的观点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和前提。我们高兴地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即我们和李志宏先生都同意:“为了理论的严密性,任何一个美学体系都必须解释审美发生问题”,只不过我们各自的解释不同罢了。因此,尽管我们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 中已从不同角度作过解释,但为了更好地求教于李志宏先生及诸位方家,我仍愿意集中和专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只不过在此之前,也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必须事先予以说明。
首先必须确定的是,承认艺术和审美有发生问题,即等于承认艺术起源于非艺术,审美起源于非审美,正如宇宙起源于非宇宙,人起源于非人(猿)。李志宏先生说“萝卜的萌芽只能长成萝卜,黄豆的萌芽只能长成黄豆”,这当然不错。但萝卜的种子和萝卜还是两回事。而且,如果要讲发生学,还不能讲萝卜起源于萝卜的种子或萝卜苗,得讲它起源于某个原本不是萝卜的物种。前者只是“成长学”,后者才是“发生学”。
其次,对于美学而言,艺术和审美的起源决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学、人类学或心理学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哲学问题。它的任务,不仅仅是描述艺术和审美如何产生,而是要回答艺术和审美的产生为什么可能和为什么必然。借用前面的比喻,就是要讲清楚那个原本不是萝卜的物种为什么有可能变成萝卜,又为什么必然地变成了萝卜。回答不了这个“可能”和“必然”,也就没有什么作为美学的艺术发生学和审美发生学。
第三,从非艺术和非审美,到艺术和审美,有一系列中间环节,正如从猿到人有“类人猿”和“类猿人”一样。“类人猿”已不是完全的猿,“类猿人”也不是真正的人,均只能视为“半猿半人”。史前艺术和审美亦然,只能叫做“前艺术”(艺术前的艺术)和“前审美”(审美前的审美)。李志宏先生说“人猿相揖别”时即已有艺术,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是已有“前艺术”。它们或者是生产劳动的形式,或者是生殖崇拜的形式,或者是图腾崇拜的形式,或者是巫术礼仪的形式,甚至干脆混为一谈,而且无不有着明确的现实的功利目的。比如狩猎的舞蹈,是为狩猎而跳的,它常常要跳到真实的野牛出现为止。又比如洞穴壁画,也是一种巫术礼仪。洞壁上某只野牛之所以一画再画,就因为每画一次,便能捕获一头野牛。同样,陶罐上之所以要画鱼蛙,是为了多生孩子;而部落里之所以要有一根雕刻着动物形象的柱子,则是为了图腾崇拜。我在拉萨大昭寺亲眼见过藏族同胞盖房子时的“打阿嘎”。那些藏族民工一边歌舞,一边用夯锤和舞步将地面夯实夯平,你说这是劳动还是艺术?在我看来,这很可能就是“前艺术”的“活化石”。
同样,在“人猿相揖别”时即已有“审美前的审美”——前审美。这大约是李志宏先生很难同意的,因为他断言“在审美发生之前,事物和艺术不可能蕴含着具有审美性质的因素”,只不过在一个我们不能准确知道时间的日子里,它们又突然有了。总之,在他那里,审美就是审美,非审美就是非审美,二者之间既无联系,也没有过渡。这就使我想起恩格斯对那些“形而上学者”的批评:“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 。李志宏先生正是这样。在他那里,审美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比如生产劳动、图腾崇拜、巫术礼仪)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比如同时是审美对象),甚至不可能具有别的东西(比如审美)的萌芽和因素。由于缺乏这样一个前提,最后,事物的审美性质和人的审美能力便只能莫名其妙地从天上掉下来。
新实践美学却能够回答审美从何产生和何以产生的问题。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回答,即:审美的发生为什么可能,审美的发生为什么必然,审美怎样发生。
〚二〛可能
什么是审美?李志宏先生认为:“审美是人类以高度智能为前提,在非功利状态下通过对事物外在形态的知觉而产生愉悦感的活动;简言之:审美是由非功利认知方式引发情感的活动。”这个定义显然问题多多。比如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就不好说是“对事物外在形态的知觉”,审美也不是认知而是体验。但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我们还是发现了双方都认可的一些观点:第一,审美是一种情感活动,因此也是一种精神活动;第二,审美是一种产生愉悦感的活动;第三,这种愉悦是无关乎功利的,是无利害而生愉快。在承认这三点共识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审美的发生为什么可能。
先说精神。精神生活是人所独有的。植物有生命无心理,动物有心理无意识,唯人类有生命、有心理、有意识、有精神生活,因为唯人类劳动。劳动作为人类独有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情感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自身便包含着物质与精神两个环节。它的有意识性、有目的性、有情感性,即是它的精神部分。只是由于分工,劳动的精神环节和物质环节才分离开来,才开始有了相对独立的精神生产和精神部门,并逐渐发展为完全独立的精神生产和精神部门。这个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新实践美学反复论证过的原理,我想已毋庸赘述。
次说情感。李志宏先生说“情感是人类乃至动物的一般的生物性功能”,这显然是混淆了情感和情绪。情绪是动物也有的,情感却为人所独有。当然,某些高等动物如类人猿已有情感的萌芽,某些家养动物如猫狗也有“类情感”反应,这正是其“类人”之处。情感与情绪的区别在于:情感有对象而情绪无对象。我们只能说爱谁恨谁,不能说兴奋谁烦闷谁。因此,情感必以意识为前提。因为意识是一个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同格结构,也只有意识才是这样一个结构。什么是自我意识?就是那种能够把自我当做对象来看待的心理能力。同样,对象意识则是能够把对象当做自我来看待的心理能力。能够把自我当做对象来看待,才能够表现情感;能够把对象当做自我来看待,才能够体验情感(比方说,把他人的悲欢离合看作自己的悲欢离合);而只有当其既能表现又能体验时,情感才是情感而不是情绪。情感决不简单的只是喜怒哀乐,更重要的是对喜怒哀乐的体验,包括在想象中体验和在回忆中体验。只有完全具备了能够在现实中、想象中和回忆中体验,并能够把他人的情感当做自己的情感来体验的能力,我们才能说这个主体具备了情感的能力。只看到猫狗恋人就说它们有情感,却全然不顾它们是否能够体验,显然是把高级的东西看低级,把复杂的东西看简单了。
要能够在现实、想象和回忆中体验,并把他人的情感看作自己的情感,就首先必须能够把自我当做对象、把对象当做自我来看待。也就是说,必须有意识。意识并不是上帝之所赋予,而恰恰是在劳动中,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中建立起来的。工具使人第一次有了“把自己划分为二”的可能——一方面是可以看作自我的对象(工具),另方面是可以看作对象的自我(工具的制造者)。由于“意识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因此,工具这个直观的对象对于意识的发生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契机。同样,它对于情感的发生也是一个关键性的契机。因为情感作为个体独有的心理体验,原本无法为他人所同感;而如果不能把他人的情感当做自己的情感来体验,情感又不成其为情感。这就只有借助一个中介,即一个“传情的媒介”来实现情感的传达,也就是通过对这个中介的共同感受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亦即“共鸣”。现在我们知道,最早充当这个中介的是工具,后来才发展为别的东西(比如千里之外送来的鹅毛),并有了专门用于情感传达的特殊工具——艺术和艺术品。
最后说超功利。李志宏先生称审美状态为“非功利”,似欠妥,应为“超功利”,即“超越功利”。后实践美学如杨春时先生甚至认为审美的本质就是超越。在审美具有超越性这一点上,我们和后实践美学并无分歧,分歧只在于杨春时先生他们拒不说明人的超越性究竟从何而来,即不承认审美有一个发生学的问题。其实,不但审美有发生学问题,超越也有。人类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能力,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上帝赋予的,更不是一生下来就有的。和审美一样,它只能产生于劳动,而且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直接相关。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目的无疑是功利的,即人的族类生存,甚至是肉体的生存,工具则不过是实现这一功利目的的手段。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指出:“手段是比外在的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锄头比由锄头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却是暂时的,并会被遗忘的”(列宁在书边批道:“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也就是说,手段和工具是具有超越性的。手段和工具一旦脱离了直接的功利目的,就会成为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存在。人的超越性便正是由它培养造就的。这其实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因此在这里也不赘述。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正是被新实践美学视为逻辑起点同时也是历史起点的劳动,使人有了意识,有了情感,有了精神生活,有了超越性,也有了审美发生的可能。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因此,我们还必须回答第二个问题:审美的发生为什么必然。
〚三〛必然
还是先从大家的共识说起。李志宏先生和我们都同意审美具有愉悦性,美感是一种愉快感,并且这种愉快是超功利或者非功利的,而审美的超越性则为杨春时先生所主张,所以杨春时先生应该也能接受上述观点。那么,剩下的问题,也就是人类何以要有一种超功利的愉悦感。换句话说,这种愉快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为什么还要要它,而且非要不可?
秘密仍在劳动那里。几乎所有批评实践美学和新实践美学的人都反对把劳动、把实践看作美学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这是因为他们对劳动缺乏深入的研究,甚至“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面形式去理解和确定” 。其实劳动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只是“苦力的干活”),它的意义在过去也远未说透。毫无疑问,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劳动一开始当然不是艺术活动,也不是审美活动,而是为了维持生存所进行的一种勤勉的生命活动,是远古原始人类在死亡线边缘上所作的一次“获生的跳跃”。即便在今天,劳动也仍然主要是创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活动,即“谋生的手段”。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如果劳动仅仅只是谋生的手段,则它和动物的生命活动就没什么两样。人要谋生,动物也要谋生,请问人的谋生(劳动)和动物的谋生(吃草、捕虫、抓老鼠)有什么不同?区别就在于人的劳动不光是谋生。除了谋生以外,它还有一层意义,就是使人成其为人,并证明人是人。这个意义和作用,我就称之为“人的确证”。
确证自己是人,这是只有人才有的心理需求。动物不必证明自己是动物。一只养尊处优的猫不必特地抓一只老鼠来证明自己是猫,一头孤独的狼也不必到别的狼那里去证明自己是狼。然而人却必须通过自己的行为,尤其是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劳动证明自己是人;也必须通过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在他人那里证明自己是人。前者就叫“自我确证”,后者则叫“相互确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动物原本是动物,而人原本不是人。既非“自然”,就得证明。因此,每个人都必须终其一生用种种方式证明自己是人。这是人的“原罪”,也是人的“宿命”。当然,这两个词都得打引号。
人不但需要确证自己是人,而且这种确证也需要确证,即确实证明自己得到了人的证明。显然,这种证明不能诉诸物理手段,只能诉诸心理感受。也就是说,正如人只有在感到幸福的时候才幸福,只有在感到自由的时候才自由,他也只有在感到被确证时才被确证。这就说明,人的确证是要由确证感来证明的。
人最早是在劳动中体验到确证感的。当一个原始人捕获了一头猎物或打制了一件工具时,他会像猫逮住了老鼠一样兴奋。但是,猫的兴奋也仅仅只是兴奋而已。它不会因此而爱上那只老鼠,不会叼着老鼠的尾巴到处炫耀。然而人却会爱上那猎物或工具,会拿着猎物的皮毛到处给人看,甚至会用它们来殉葬。因为这工具和猎物已足以证明他是人,是他证明自己的“物证”。同样,这时他的心理也不再仅仅是动物也有的兴奋(情绪),而是人才有的愉悦和爱(情感)。
因此,当我们说到人的愉悦时,必须对它的构成进行分析。就原始人类的原始劳动而言,这种愉悦常常包含着两种成分。一种是由于生存需要和谋生目的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愉快(即满足感),这是功利性的愉快感;另一种则是由于能够确证自己是人而引起的愉快(即确证感),这是超功利的愉快感。前者动物也有,后者为人所独能。当然,人的确证也可以广义地说成是一种功利目的,但不是直接的功利目的,甚至人自己还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目的,是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目的却实际上合目的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因此叫做“超功利”,即“超越直接功利”。
超功利不等于没有用,更不等于可有可无。由于人的确证在实质上是人的“第一需要”,因此,确证感还有“大用”,而且不可或缺。只不过因为它不以满足直接功利为目的,所以看起来好像没有用,也所以只能叫做“超功利”,不能叫做“非功利”。同样,一个对象如果能够使我们体验到确证感,那么,我们就不会只叫“好”(有用),还会叫“美”(愉快),至少同时会叫“美”。因为只有确证感和美感一样,是一种超功利的愉快感,因此一个能够确证人是人的对象便一定会被看作审美对象。事实上,当一个原始人制造的工具不但满足了他生存的需要,而且使他体验到了确证感的时候,这件工具就不但是“好”,而且同时是“美”了。只不过在这时,它还主要是“好”,不是“美”。只有当人们完全超越了功利目的,不但能够在自己创造的对象那里,而且能够在其他对象甚至是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对象那里也体验到这样一种超功利的愉快感时,审美才真正从非审美和前审美变成了审美。从非审美和前审美到审美,其间当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和一系列中间环节,但审美发生的必然性,却毋庸置疑地就在人的确证的必须性那里。
〚四〛过程
现在,我们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审美怎样发生。前已说过,审美起源于非审美。具体地说,就是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中的审美性因素。劳动不是审美活动,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也不是审美对象,却能够使人体验到因自我确证而产生的愉悦,即确证感。它作为第一种超越了直接功利目的的愉快感,就是美感的原始形态和蕴含在劳动中的审美性因素。
美感的原始形态要变成现代形态 ,蕴含在劳动中的审美性因素要变成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作为一种独立精神生活的审美,当然非一日之功。其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在于情感的性质。我们知道,美感也好,确证感也好,都是一种情感,而一切情感都是“同情感”。所谓“同情”,并非道德意义上的“怜悯”,而是指“相同的情感”。爱是一种肯定性的同情感,恨则是一种否定性的同情感。一个产生了爱或者充满仇恨的人,总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把对方看作是和自己一样在爱着或者一样在恨着的人,从而“越看越可爱”或者“越看越可恨”。否则,就会“爱不下去”,或者“恨不起来”。这也就等于说,没有同情(相同的情感),情感就不成其为情感。
因此,情感从本质上讲是可以传达也必须传达的,而经过了传达亦即对象化了的情感就是美感。美感不是一般情感,而是“高级情感”。之所以“高级”,则是因为它经过了传达,对象化了。所谓“对象化”,无非是通过“移情”把自己的情感看作了对象的性质,以至于人们常常误以为美感是从对象那里获得的。其实,“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不过是“想当然”,是“料”。但是,没有这个“想当然”,没有这个“料”,就不能审美,因此又是“理所当然”,是“应”。说到底,无非“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情感的对象化既然只不过是“移情”,那么,它就与对象的实体无关,而只与其形式有关,比如“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在这里,蜡烛有没有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垂泪”的形式。有此形式,便可移情。于是,美感就最终变成了形式感,也就是情调。情调是人的一种高级情绪,只不过我们不把它叫做情绪,而叫做情调。它与一般低级情绪的区别在于:情绪感觉的是“内容”(比如天气的冷热),情调感觉的是“形式”,比如山峰的挺拔感,原野的辽阔感,燕子的轻盈感,殿堂的肃穆感。这些都只与对象的形式有关,因此又叫“形式感”。
审美就是体验形式感,比如田园情调、都市情调、古典情调、现代情调,贝多芬乐曲中的月光情调,康斯太勃尔笔下的英格兰乡村情调。实际上,在与艺术品猝然相遇又怦然心动的那一刻,我们是来不及仔细琢磨它的意义和结构的。我们总是“一下子”就被某种“说不清”的东西感动和震撼了。这东西就是情调,就是形式感,是那朴拙的造型,细腻的质感;是那如歌的行板,如瀑的笔势;是那如海苍山之上的如血残阳,那旗卷西风月照征程的雁叫霜晨,“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就连被李志宏先生视为“非审美”的原始艺术,也因其充满蛮荒气息和野性活力的情调而对我们具有审美魅力。
对形式感的审美体验具有直接性,它在心理过程上表现为一种直觉。因此,它好像不是体验,而是认识,即对对象形式结构的一种纯客观的冷静的整体把握。这也是李志宏先生误将审美看作认知的原因。但必须指出,情调看起来是“对对象的情感”,实质上却是“对情感的情感”,是情感的形式或调子。因此它决不能等同于一般低级情绪,也因此不能叫“情绪”,而应该叫“情调”。
当人类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生活从对确证感和一般同情感的体验上升到对形式感的体验时,审美就完成了它从非审美和前审美到纯粹审美的全过程。与之相对应,艺术也完成了它从非艺术到前艺术再到纯粹艺术的过程。在这里,劳动的异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异化劳动是相对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而言,而后者的特征,就是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对象、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异化劳动则使之分离。正是由于这种分离,在艺术领域,创作与欣赏也分离了,分离为生产者(艺术家)和消费者(欣赏者);而在审美领域,则使审美对象不必再是审美主体自己创造的对象(如工具和猎物)。它甚至不必让人直接感到它是可以确证人之为人的,只要它的外在形式能够引起超功利的愉快感,便一而足矣(但一般地说,明确让人感到“拒绝确证”的东西如粪便、死尸,仍很难成为审美对象)。这当然又是一个必须专文论述的问题。不过,对于审美发生学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都已作了回答,相信李志宏先生应该不会再说新实践美学“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也不会再说我们“顾此失彼,不能一以贯之”了吧?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