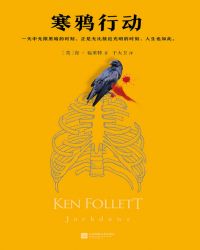第8章 第二天 1944年5月29日,星期一(1)
06
迪特尔·法兰克开着那辆希斯巴诺-苏莎趁着黑夜赶路,同行的是他的年轻助手汉斯·黑塞中尉。汽车已开了十年,但它结实的十一升发动机马力充沛,毫无倦意。昨天晚上,迪特尔在后挡泥板上发现了几个排成一条优美曲线的弹孔,那是圣-塞西勒广场交火留下的纪念品,但车的机械性能没有受损,而他认为这几个弹孔给汽车增添了魅力,就像一个普鲁士军官经过决斗脸颊上留下的疤痕。
开车穿过巴黎漆黑的街道时,黑塞中尉将大灯遮上,当他们来到去诺曼底的路上后才取下了罩子。他们轮流开车,每人开两个小时,尽管黑塞情愿全程都让他一个人开。他喜欢这车,也像崇拜英雄一般崇拜它的主人。
迪特尔坐在乘客座位上,车灯前不断延伸的乡间道路给他催了眠。他似睡非睡,想象着自己的未来。盟军会夺回法国,把占领军赶出去吗?想到德国可能战败,他难免心情低落。也许会有某种和平解决方式,德国放弃法国和波兰,但保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但这似乎也好不了多少。他发现,自打他在巴黎生活,与斯蒂芬妮一道经历了刺激和放纵之后,很难想象再回到科隆,跟自己的妻子和家人一起过原来那种日子了。不论是对德国还是对迪特尔,唯一完美的结局就是让隆美尔的军队将侵入者推回大海去。
在潮湿的黎明来临之前,黑塞开进了一个中世纪的小村拉罗什-居雍,它位于巴黎和鲁昂之间的塞纳河上。他在村口的路障边停下,但岗哨知道他们要来,很快就放行了。他们默默经过一座座大门紧闭的房子,到达一座古老城堡大门口的另一个检查站。最后,他们把车停在一个鹅卵石铺地的大院子里。迪特尔让黑塞留在车上,自己走进大楼。
德军西部战区总司令格尔德·冯·伦德斯泰特元帅是位来自旧军官阶层的高级将领,值得信赖。他的手下是负责法国海岸防御的埃尔温·隆美尔元帅。拉罗什-居雍城堡是隆美尔的总部。
迪特尔·法兰克感到自己与隆美尔很亲近。两人都是教师的儿子——隆美尔的父亲曾是位校长——因此都能从冯·伦德斯泰特一类人身上感到德国军队那种冷冰冰的傲慢气息。但除此之外,他们又有很大不同。迪特尔纵情逸乐,很是欣赏法国提供给他的所有文化和感官享受。隆美尔则是一个沉湎于工作的人,不抽烟不喝酒,常常忘记吃饭。他只结识过一个女友并娶她为妻,一天要给她写三封信。
在大厅里,迪特尔见到了隆美尔的副官沃尔特·莫德尔少校,这是一个性格冰冷、头脑极其复杂的人。迪特尔尊重这个人,但无法喜欢他。他们在前一天的半夜里通过电话。迪特尔简单说了一下他在盖世太保那儿遇到的问题,说自己希望尽快见一见隆美尔。“早上四点到这儿来。”莫德尔说。隆美尔总是在凌晨四点钟出现在他的办公桌前。
现在,迪特尔怀疑自己是否该这么做。隆美尔可能会说:“你怎么竟敢拿这种琐碎事来打扰我?”迪特尔觉得隆美尔不会。指挥官总是喜欢掌握细枝末节,他几乎可以肯定隆美尔会支持他,答应他的要求。不过这也难说,尤其是在指挥官备受压力困扰之时。
莫德尔轻轻点了一下头,算作打招呼:“他想现在就见你。跟我来。”
两人经过走廊时,迪特尔说:“意大利那边有什么消息?”
“都是坏消息。”莫德尔说,“我们要撤出阿尔塞。”
迪特尔表情坚忍地点了点头。德国人在拼命战斗,但他们仍然无法阻止敌人向北前进。
一分钟后迪特尔走进隆美尔的办公室,这是位于一楼的一个宽敞华丽的大房间。迪特尔注意到一面墙上挂着一块价值连城的17世纪哥白林挂毯,顿时心生羡慕。这里办公用具不多,但几把椅子和一张巨大的古董桌子,在迪特尔看来可能与挂毯一样古老。桌子上放着一盏灯,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小个儿男人,发际线已退后,长着一头淡棕色的头发。
莫德尔说:“法兰克少校来了,元帅。”
迪特尔紧张地等在一旁。隆美尔继续读了一会儿,然后在一张纸上做了个记号,那姿态就像一个银行经理在查看他最最重要顾客的往来账目。而当他抬起头来,立刻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迪特尔以前见过这张脸,但每一次见到他,都让迪特尔感到气势压人。这是一张拳击手的脸孔,长着扁平的鼻子和宽宽的下巴,靠得很近的双眼,整张脸上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挑衅神情,这让隆美尔成了一位传奇般的指挥官。迪特尔记得隆美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故事,那是他的第一场战役。他带领着三个人组成的先遣队遭遇二十人的法国部队。他没有撤退寻求增援,而是朝对方开火,勇敢地冲入敌阵。他幸运地活了下来——但迪特尔记得拿破仑的名言:“我要的就是幸运的将军。”从那儿以后,隆美尔就一直喜欢大胆地突然袭击,而不是谨慎地计划进攻。他与他的沙漠对手蒙哥马利是截然相反的两极,后者的观点是直到有把握取胜才发动进攻。
“坐下,法兰克。”隆美尔爽快地说,“你有什么想法?”
迪特尔已做过一番排练,他说:“按照您的指示,我走访了可能受抵抗力量攻击的关键设施,改进了这些地方的安全防卫。”
“很好。”
“我也一直在设法评估抵抗组织会造成严重破坏的可能性。他们会真正牵制我们,应对入侵吗?”
“你的结论呢?”
“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糟。”
隆美尔厌恶地哼了一声,好像一个令人不快的猜测得到了证实。“你的理由是什么?”
隆美尔不会一口咬掉他的脑袋,这让迪特尔稍稍放松了点儿。他说起了昨天在圣-塞西勒遭遇的进攻,一一陈述了抵抗组织独特的计划,大量的武器弹药,最主要的是那些战士勇猛顽强。唯一没说的细节是那个美丽的金发姑娘。
隆美尔站起身,朝那块挂毯走过去。他眼睛盯着它,但迪特尔相信他不是在看挂毯。“我担心的就是这个。”隆美尔说,他声音很轻,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我可以击退一次进攻,哪怕我只有几支队伍,只要保持灵活机动就行——但如果我的通信垮了,我就会必输无疑。”
莫德尔同意地点点头。
迪特尔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利用这次攻击电话交换站事件,把它变成一次机会。”
隆美尔转过脸来,苦笑了一下。“我的上帝,我希望我的所有军官都像你一样。说下去,你想怎么做?”
迪特尔感到这次会面已经按照他的意思进行了。“如果我能审问那些被俘的囚犯,他们就会让我找到其他组织。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在入侵前重创抵抗阵线。”
隆美尔有些怀疑。“听起来有点儿自我夸大。”迪特尔的心往下一沉,隆美尔继续说:“如果别人说这种话,我会把他轰走。但我记得你在沙漠工作中的成绩。你能让那些人不知不觉招出口供,连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
迪特尔很高兴,他抓住自己的优势,继续说:“不幸的是,盖世太保拒绝让我审问那些囚犯。”
“他们就是这么愚蠢。”
“我需要您的干预。”
“当然可以。”隆美尔转向莫德尔,“给福煦大道打个电话。”盖世太保的法国总部设在巴黎福煦大道84号。“告诉他们,法兰克少校今天要审问犯人,要不就让贝希特斯加登那儿的人给他们打电话。”他指的是希特勒的巴伐利亚要塞。陆军元帅拥有直接接触希特勒的特权,该用的时候隆美尔从不犹豫。
“好的。”莫德尔说。
隆美尔绕着他17世纪的桌子走了一圈,又坐了下来。“有消息请立即通知我,法兰克。”他说,随后又去看他的文件了。
迪特尔和莫德尔离开了房间。
莫德尔把迪特尔送到城堡大门口。
外面,仍是到处漆黑一片。
07
弗立克降落在伦敦以北五十英里的坦普斯福德,这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简易机场,附近是贝德福德郡的桑迪村。仅凭嘴巴里那夜晚湿冷空气的味道,她就知道自己回到了英国。她爱法国,但这里是她的家。
走在机场上,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度完假返回时的情景。她母亲一看到自己家的房子,总会说出那句话:“外出不错,但回家更好。”在这最不平常的时刻,母亲的话涌上了她的脑际。
一个身穿急救护士队下士军服的年轻女子在等她,开一辆大马力的捷豹准备将她送到伦敦。“真是奢侈啊。”弗立克说着,坐到车里的真皮座椅上。
“我直接带你到果园宫,”司机说,“他们在等着听你的汇报。”
弗立克揉了揉眼睛。“老天,”她寻求同情般地说,“他们不觉得我得睡会儿觉吗?”
司机没有搭茬,而是问道:“任务执行得很顺利吧,少校?”
“全他娘砸。”
“对不起,什么?”
“全他娘砸,”弗立克重复了一句,“这是句缩略语,也就是情况全他娘的搞砸了的意思。”
那女子不说话了。弗立克觉得自己的话让她尴尬。不错,她沮丧地想,终究还有受不了这种军营粗口的女孩。
当汽车快速通过赫特福德郡的斯蒂夫尼奇和奈柏沃斯村时,天已破晓。弗立克看着窗外掠过的房屋和屋前园子里的蔬菜,看见乡村邮局那脾气欠佳的女局长在没好气地施舍小额邮票,还看见各式各样的小酒馆,那里面尽是温乎乎的啤酒和快散架了的钢琴。纳粹没能打到这么远的地方,真让她深深感到庆幸。
这种感觉让她更加铁了心回到法国去。她要寻找机会再次袭击城堡。她想到那些留在圣-塞西勒的人们:阿尔伯特、年轻的贝特朗、美丽的吉娜维芙以及其他或战死或被俘的战士们。她想到了他们的家人,这些人正在被失去亲人的痛苦和焦虑所折磨。她痛下决心,绝对不让他们白白牺牲,一切付出终究要求得到结果。
她应该立刻投入行动。马上让她做汇报更好,今天她就有机会提出自己的新计划。特别行动处的人一开始会谨慎对待,因为谁也没有派过清一色都是女性的小组执行这类任务。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阻碍。不过干什么事情都会有阻碍的。
他们到达伦敦北部郊区的时候,天已经大亮,到处是起早干活的人,邮差和送奶工在递送货物,火车司机和公交车售票员正徒步赶去上班。战争的迹象随处可见:反对浪费的招贴画,屠夫的窗口挂的“今天没有肉”的牌子,一个开着垃圾车的女人,整排被炸成废墟的小房子。但这里没人会拦住弗立克,没人会要她出示证件,没人会把她投入牢房,拷打她交出情报,再把她用拉牲口的卡车送到某个集中营,一直待在那里饿死。她感到卧底生活里的那种高度紧张正慢慢缓解,她往后倒在汽车座椅上,闭起了眼睛。
她醒来的时候,汽车已经进了贝克街。车子走过了64号。特工一般不进总部大楼,万一受到审问,他们便不会透露其中的秘密。事实上,很多特工都不知道它的地址。汽车转到了波特曼广场,在那座公寓楼——果园宫外面停了下来。
司机跳下车,为她打开车门。
弗立克走进里面,去找特别行动处的那一层。见到珀西·斯威特时,她一下子来了精神。这是一位五十岁的男子,秃头,上唇留着牙刷般的胡子。他像父亲一般喜欢弗立克。他穿着便装,两人都没有敬礼,特别行动处的人都没耐心讲究军事礼节。
“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事情不妙。”珀西说。
他同情的嗓音让弗立克再也忍不住了,刚发生的悲剧骤然间压垮了她,她一下子哭了起来。珀西用胳膊搂住她,拍着她的后背。她把脸埋在他的老花呢夹克里。“没事了,”他说,“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哦,上帝,对不起,我怎么成了这样哭哭啼啼的女孩。”
“我希望我的手下都是你这种女孩。”珀西话里有话地说。
她离开珀西的怀抱,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请别在意。”
他转过身去,用一块大手帕擤了擤鼻子。“是喝茶还是喝威士忌?”他问。
“还是茶吧。”她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屋子的陈设破破烂烂,是1940年匆忙配置的,以后就再也没换过。一张不值钱的桌子,一块破旧的地毯,还有几把配不成对的椅子。她一下子陷在松垮垮的扶手椅里。“沾了酒我会睡着的。”
她看着珀西沏茶。他这人很有同情心,但也会十分强硬。他在一战中获过战功,二十几岁时领导过工人罢工闹事,他参加了1936年的卡波街战役[5],与东伦敦佬们袭击了试图穿过伦敦东头犹太人街区的法西斯。他会就她的计划提出各种尖锐细致的问题,但他也会十分开明,听取别人的见解。
他把一杯茶递给她,外加牛奶和糖。“今天上午晚些时候有个会议,”他说,“我要在九点钟以前把简报送给上司。时间有点儿紧。”
她喝了一口甜茶,感觉到摄入的能量带来的快意。她把在圣-塞西勒广场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他坐在办公桌边,用尖尖的铅笔记着笔记。“我本应该放弃这次任务,”她最后说,“安托瓦内特对提供的情报有怀疑,我本应该推迟突击,给你发一条无线电通知,说我们寡不敌众。”
珀西悲哀地摇摇头说:“可是没有时间推迟。要不了几天就要进攻了。就算你向我们发出请求,我估计结果也没什么两样。我们能干什么?我们无法给你派更多人手。我想我们只能命令你不顾一切往前冲。必须做出尝试,电话交换站太重要了。”
“嗯,这倒是种安慰。”想到不必认为阿尔伯特是为了她的战术失误而死,弗立克心情稍稍好过一些了,但这并不能让死人复生。
“米歇尔没事吧?”珀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