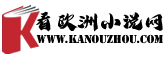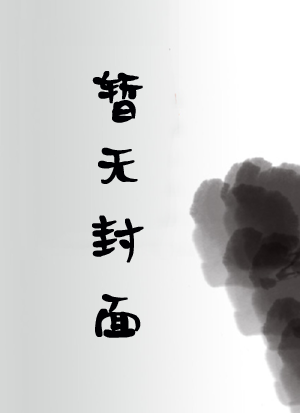陶者
陶者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此诗讽刺剥削制度下不劳而获、劳而不获的极不合理的现象。“陶者”就是砖瓦匠、泥瓦匠,这首诗是代鸣不平的。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两句写劳而不获的现象。这种题材,在历代民歌中并不少见。早于此诗的,如汉代刘安《淮南子·说林训》有“屠者藿羹,车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处狭庐——为者不得用,用者不肯为”的谣谚。晚于此诗的,如明清时有“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喝淡汤;种田的,吃米糠”的歌谣。“陶尽”二句所咏,与“陶人用缺盆”“泥瓦匠,住草房”之所慨叹的并无二致。一个做砖瓦匠的人,却没有住过瓦房,这种事儿既是咄咄怪事,又那么司空见惯,岂不是存在即荒谬么?《红楼梦》第七十七回王夫人所谓“卖油的娘子水梳头”,也是这个意思。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两句写不劳而获的现象。与上述民歌只写一端的做法不同,这首诗说罢劳而不获,便说不劳而获。对比鲜明,发人深省。“十指不沾泥”之所指,非指一切不沾泥的人,而特指所谓“劳心者”,孟子的名言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饲)人,治人者食(饲)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首诗的可贵,在于质疑这种理论的正义性和公平性,并不认为那么天经地义。“十指不沾泥”,在语言上很生动、很形象、很民间。“鳞鳞”以状瓦房屋顶的鳞次栉比,与上文“无片瓦”形成巨大反差;“大厦”与上文的“屋”形成巨大的反差。
常言道,记者是社会的良知,在没有记者的时代,诗人就充当了记者的角色,充当了社会的良知。这首诗可与同时代张俞《蚕妇》(“昨日入城市”)参读。二诗手法相近,不过张诗以第一人称叙事,控诉的意味较明。这首诗叙事角度比较含蓄,控诉的力度却并不亚于张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