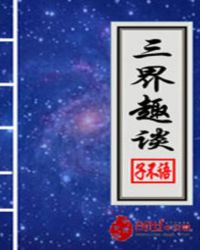元惟扬是不信符咒的,见她半信半疑,还笑道:“果然你们女子爱信这般东西,其实这当真是胡诌了。你且想,这东西十有*是那个人安排的,她怎会用当真能害到人的东西牵扯你们两个?”
赵霜意看看他,只是笑了笑,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他的意思,心中却大大翻了个白眼――这些个男人呐,总觉得女人爱搞迷信,就像他们在现代的部分同胞也很喜欢一口咬定女人都爱星座塔罗牌一样。不过若他们都这么以为倒也省事,那审案子的看了季家祠堂里的这玩意儿,肯定也觉得季雪川信这手段啊。
果然,这诅咒的符纸偶人一出来,消息就传遍了朝野。赵尚书再出场时头上都顶着一行大字――委屈得不要不要的。季将军原还托了人去寻赵尚书等旧日友人,哪怕只能替他辩白一下这刺杀太子的事儿和忠心耿耿的他无干也好,可转眼便听狱吏说家中搜出了这玩意儿,登时恨得险些昏过去。
那赵尚书何等疼爱两个女儿!他要是知道季家的姑娘咒他的千金生个孩子母子双亡,他没亲手来牢里剁了他们都算是遵纪守法了。指望他帮季家说话,还不如指望皇帝和太子怜悯他征战一生许他回乡安度晚年呢。他咬着牙打听自家那孽种怎样了,却听狱吏道季雪川吃吃睡睡问什么招什么日子过得格外滋润。
这却叫他如何不怒?直咆哮道:“这孽障竟如此!她害了一家老小,就不怕祖宗不饶她吗?”
那狱卒却笑道:“季将军,您家那位千金,是因了从实招认您有心扶持废太子才有吃有喝的,她怎么想,咱们是不知道,然而这口供落成,证据鲜明,再想不认,可就不能了。除非是陛下开恩,否则您这案子,是翻不了了。那还不若早些承认了,趁着有几日好活,混他几日吃喝……”
他沉默了许久,终于道:“这话,你对我儿说去,他们若是招认了,还能得几口好酒菜。我么……若是有拷打,冲着我来就是。”
那狱卒冲他一挑拇指:“将军果然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只是这话小的可不敢和少爷说去,若是叫人知晓了,说小的撺掇犯人……那小的这一家老少可就没人养了。这么说吧,将军,您这剩下的日子,想要什么酒菜,只管吩咐小的便是。”
“我不想要酒菜……只想见川儿一面。”他低声道,声音里有压不住的愤怒:“我只要问她一句,她为什么这么做!”
那狱卒却是犹疑了,半晌才道:“将军,这话,您得过审的时候问二姑娘。女囚是进不来这边儿牢狱的……”
他说完这一句,便等着他心中那“铁骨铮铮”的将军答话,但对方却只是依靠在囚室的木栏上,闭着眼睛,挥了挥手。
从这一日起,他再也没说过一句话,直到皇帝赐下毒酒,道他曾与社稷有大功,不忍叫他受刀斧加身,赐个全尸时,他才笑了一声,将毒酒一饮而尽,就那么去了。狱卒在一边儿看着,听着人临死前的挣扎声,连头都不敢抬,过了好一会儿,那送毒酒来的内监才叹了一口气,道:“了了,咱家回去复命了。”
“公公,他这尸首……”
“尸首?陛下说了,给他们父子留个全尸……那就许人来安葬吧。”那太监道:“父子两个一道,也好做个伴。”
至于田姨娘和季雪川,却是难逃凌迟了,田姨娘一路嚎骂季雪川,叫百姓看了个热闹,季雪川却是面带微笑,镇定自若,上了囚车时仍是云淡风轻模样,囚衣亦整齐,叫围观百姓看着,倒是各个都觉得这季二姑娘着实淡定。饶是她一身的罪过,可那神色,竟是半点儿也不悔罪似的。
亦有人唾弃她不明事理的,亦有人讲些花边儿消息的,人群纷纷攘攘来看这敢行刺太子的女人。道边的酒楼上,一扇半开的窗后,赵霜意却始终坐着,握着杯子的手不停地颤抖。
“你不看她一眼?”元惟扬立在一边儿,道。
赵霜意犹豫了片刻,将手中的茶盏放下,站到了窗边,向下眺望。季雪川的眼神是空的,脸上的笑容却恬淡知足,竟是比赵霜意什么时候见到的她都多了一分从容。
那是实现了愿望的人才会有的神色。赵霜意忍不住去想,季雪川的愿望究竟是什么呢?她是要报仇的人,可她是向谁报仇呢……如今丢了性命的,也只有那对男女和季照辉,季雪竹还在宫中做着她的良娣,哪怕一生无宠,到底能活下去,那个前生亲手杀了她的冀王也好好地做太子,断了一只手也并不如何。至于她和赵之蓁,更是半点儿影响都没有,这效果虽可归功于赵双宜的打算精密,可季雪川要报复的人,终究没有报复干净啊。
这样就已经无所求了么?赵霜意抓着窗棂,看着那囚笼摇摇晃晃路过大街,看着季雪川脸上像一朵素色花一般绽开的微笑,便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片迷茫之中。
她一直以为是敌人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这个时候,她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想去找到赵双宜,问一问她到底同季雪川说了什么――说什么才能让这个女人将复仇的对象圈回自己家中,不再冲着她们这些人?
囚车过去了,看热闹的百姓也过去了,街道重新空旷下来。元惟扬在她面前合上窗,轻声道:“回去吧。你不会想去看她受刑的,是不是?”
“不去。”她轻声重复,又道:“或许,她可以不用死的。三爷,若是……若她看开一点,不与别人为难,也许不至于到拼上性命才能报复那一家人,她可以活得不比别人差。”
“或许,同归于尽便是她的愿望。”元惟扬眯起眼,轻声道:“现下想想,她与我不同的。我想……和你一起,和家人一起好好过一辈子,可她没有可以当做家人的人了。也许她重活一生只不过是想将那些人一并拖入火狱……这么说,倒真是得偿所愿,死无可恨。”
赵霜意沉默良久,伸手握住了他的手:“我陪你。”
她和他相遇实在太过离奇,一个穿越的遇到一个重生的,万中无一的平方。他也罢,她也罢,都不是季雪川那般报个仇就死的人,无论过去走了多少崎岖做了多少该做的不该做的,今后总该要相伴好生过下去才是。
元惟扬看着她,好一阵子之后嘴角微微挑了起来,点了头,道:“你既然应了,便一定要做到。”
※
“你与她,都说过些什么?我原本以为,她会想杀了我。”赵霜意看着面前仍然瘦弱的少女,轻声道。
“她大概一直都恨你,只不过渐渐不想杀了你罢了。”赵双宜笑道。她穿一身青色的布衣,头发披散下来,仍旧有些枯黄,那是久病的痕迹。
“为什么?”
“因为用命去恨的人只能有那么一个啊……她恨了她爹,就没有那么多力气去恨别人了。她只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报复一回,也就会把自己赔进去了。”赵双宜道:“若是把这次机会花在你身上,她哪儿还有第二条命去报复她爹和那个田姨娘?”
“可她还差一点儿,行刺就成功了……”
“差一点?是差许多,成功不了的。”赵双宜轻声道:“她不忍心伤他。若真下定决心,那□□发作如此迅猛,挠脖颈脸面岂不是无药可救?她却只伤了他的手……说到底,只有那一刺她才有杀心,那一刺不中,也就,也就罢了。”
赵霜意沉默了,她回想着那一日的情形――是啊,只有那一刺是真心想杀了这个彻底将她忘在了脑后的男人的,失去了那一次机会,季雪川就先失了心……她的痛苦悲伤像漫上海堤的潮水,先淹没了她。而她记挂的人在她面前只问了一句话,之后由着她作死,由着她去死。
“倒也多亏了你,”许久她才哑声道:“不然她即便杀不了太子,也可以将赵家拖下去一并毁了……若不是你留下那符纸……”
“那符纸是我安排的,却不是我留的,”赵双宜道:“留下它的,是季雪川自己。”
“什么?!”
“藏符纸的婢女说过……那东西,季雪川早就发现了,可她没有拿走,也没有毁掉,就放在那里。不知道她怎么想的……或许那时她以为季雪竹放的,今后能用来当做把柄,或许她已经知道了内情却不想再做什么……到底,赵双宜曾经是季雪川的朋友啊。连我也猜不透她的想法,我只知道,她和我一样,是不该留在这里的人。”赵双宜说着,手轻轻拂过案几上的一只盒子,盒子里是剪子和剃刀:“四堂姐,你该走了。时辰快到了,师父要来了。你是侯府夫人,不该来这样的场合。”
赵霜意深吸一口气,再一叹,终于站起身,走了出去。在赵善好家的门口,她与一名青年尼姑相遇,目光相撞的一刻,对方停下,念一声佛号,而她也止步,深深向她行了个礼。
“夫人为什么和那位师父行礼?”上了马车,丽藻问道。
“她的神色了无所求,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