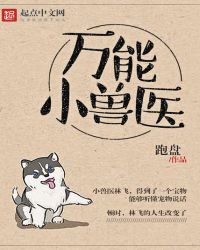周南·关雎
周南·关雎关关雎(jū)鸠,在河之洲。窈(yǎo)窕(tiǎo)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将文学的终极原因归结到性恋的说法看似偏颇,其实信而有征。“风诗者,固闾阎风土男女情思之作也。”(司马迁)在民歌中,情歌据有优势地位,所谓“无郎无姊不成歌”。理由很简单,民歌多属劳动者之歌,什么歌能提高劳动兴趣就唱什么,什么歌能提高劳动效率就唱什么,还有什么比情歌更能提高劳动兴趣、劳动效率,又更能消除疲劳的呢?
排在《诗经》第一篇的《周南·关雎》是情歌;具体地说,是恋歌;更具体地说,是写男子的单相思。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话有点费解。我宁可这样认为:因为单相思是普遍存在的情感,显然也是正常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思无邪”了。何必一定要牵扯什么“后妃之德”(《毛诗序》)呢。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诗中主题句,《毛诗序》谓“乐得淑女,以配君子”。鲁迅调侃地释为“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陈子展说“当视为才子佳人风怀作品之权舆”(《诗经直解》)。都不错,但讲得太城市化了,不类风土之音。不如用高踞当代情歌排行榜首的《康定情歌》中的两句来诠释,更为神似:“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
“上河里鸭子下河里鹅,一对对毛眼眼望哥哥”,这首《信天游》以水禽起兴的手法所来自远,可追溯到《关雎》。河边洲岛上,水鸟儿作双成对,雄雌和鸣,引起诗人的感兴,如果按“关雎”即鱼鹰的说法(毛奇龄),则此二句还有以水鸟捕鱼隐射男子求爱之义。诗中男子以“君子”自谓,而“琴瑟”“钟鼓”之乐都非平民之乐(《墨子》),可以推测抒情主人公为一贵族青年。《诗经》的好几首诗中,思慕的男女,往往被河水隔断。何新认为,这与源于性禁忌的古代学宫制度有关——男子到达八岁就得离开父母膝下,就读于学宫,这种学宫又叫辟雍(即避宫)和明堂,一律建在城郊,有水三面或四面环绕,使之与外界隔绝,故又称泮宫(泮水园即校园),直到成丁举行“冠礼”。所以诗中的河水既是一种象征(爱情遇到的间阻),又是一种纪实(参《诸神的起源·第九章》)。如其说法成立,莫非《关雎》写的是古代校园中大学生之烦恼?
“窈窕淑女”的身份,余冠英据“参差荇菜”在诗中三复斯言,认为当是“河边一位采荇菜的姑娘”,不无道理。姑娘采荇的美妙姿态,摄印入那青年的脑中,是难以磨灭了。而“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不仅可使人想见伊人倩影,而且也似乎有以勉力求取荇菜,隐喻对其人的执着相思之义。写采荇菜,而意在采荇的人。诗中写男子的单恋十分坦率,醒也想、梦也想。“寤寐求之”紧接“求之不得”云云,用“顶真格”,已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感,而“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更通过失眠,将相思之苦推进一层。钱锺书说:“《太平乐府》卷一乔梦符《蟾宫曲·寄远》:‘饭不沾匙,睡如翻饼’,下句足以笺‘辗转反侧’也。”(《管锥编》一)
与每一种满足都会降低其崇拜相反,爱的渴求却能导致爱的升华。诗中陷入情网不能自拔的那位青年,于是做起了美妙的“白日梦”,在想象中和他的爱人美满结合。又是“琴瑟友之”,又是“钟鼓乐之”。这诚然是一场虚构的热闹,一座美丽的空中楼阁,但那青年在一刹间满足了,读者不禁为之陶然。这升华的境界,便远离了性的目标,成为热诚、挚爱、欢乐、和谐的“结合”(或以为诗的最后一章,实写得之为欢,本文不取此说)。有一种概括,认为中国写情文学中色性的成分居多,揆之《诗经》包括《关雎》在内的大量情诗,似不尽然。
《关雎》“乐而不淫”有其历史原因。大量史料告诉我们,诗经时代婚俗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其时封建礼教为基础的专偶婚制尚未稳固形成,而人们还享有较多性爱的原始自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方才产生了如同《关雎》那样的热烈奔放的情歌。这里毫无顾忌的爱情直白,已凝聚成一种原始的美。而为儒学礼教统治下的汉儒宋儒们感到十分困惑,百思而不得其解。“《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这话同样出之《毛诗序》,便很费解,定非诗之本旨。
《关雎》章法在诗经中别具一格。诗经本多叠咏体,但常见的是三章叠咏、两章联咏,像《关雎》这样第二章和第四五章跳格叠咏,是仅见的。日本青木正儿曾怀疑是误合两诗而成(详《支那文学艺术考》),但“窈窕淑女”通贯全诗,“寤寐求之”与“求之不得”顶针衔接,妙合无垠,而诗经中叠咏体间有首章或他章不叠的现象屡见,故错简之说很难成立。二、四、五章的叠咏除却描写荇菜的兴语不论,“看他窈窕淑女,三章说四遍”(钟惺《评点诗经》),这活脱是热恋中男子对不知名的爱人的反复叨念,神似《董西厢》妙语所说:“锦笺本传自吟诗,张张写遍莺莺字。”
“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苏轼)。若下一转语,便有“说诗必此诗,定知非解人”。懂得这番道理,来看《关雎》诗中的单相思,又不仅是单恋而已。诗人于爱的对象“寤寐求之”式的执着追求,及其在现实中“求之不得”,便于理想中“友之”“乐之”的实现方式,均构成一种境界,一种超越本文的象征意蕴,从而能够兴发读者引譬连类的联想。我们不由会联想到风诗中的其他作品如《汉广》《蒹葭》,联想到《离骚》,其中所写的“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苦恼,“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迷惘,及“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劲头;不由会联想到古代神话对世界的浪漫征服和把握的方式;甚而联想到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不安现状,通过心灵与思辨追求美与自由、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历程。诗情一旦与哲理结合,便给世代读者以回味无穷的审美愉快。
这,或许就是包括《关雎》在内的风诗名篇的艺术奥秘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