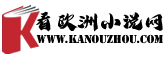傻四叔文玮万没想到,安氏会说出这样的一翻话来,顿时慌张,呐呐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安氏却是看也不看她,坐在罗汉床上,依旧浅笑道:“四爷什么意思,我不想知道,四爷给个话,我只照做就是了。”
从前安氏哪怕不闹,哪怕生气或者冷淡,再或者横眉怒目,他既便怕她生气,也没有这一刻的安氏,让他觉得如坠冰窟。他只觉得自己再不敢在安氏面前站下去,一刻也不想待了。
只因他怕安氏再说出什么让他更怕的话来。
和离,那是他想也不愿意去想的事情,更何况做?
“四爷知道来责问四奶奶,怎不晓得问问那林姨娘都做了什么?”
丫鬟喜鹊听不下去,为安氏辩解。
安氏听了,却斥道:“喜鹊,住口。”
喜鹊本还想再说,被安氏这一喝,也不敢多嘴了。
文玮此时满心里都是“和离”两个字,喜鹊的话他是半个字也没有听进去,反倒是转过身,仓皇的逃一般的奔出了安氏的屋里。
这林姨娘被打,安氏受伤,小两口要和离的事情,自然瞒不过祖母那里,老祖母也只能叹气。
小儿子闹了一场,倒是轻省的躲了出去,老祖母总不好直接去处置儿子的妾室,等安氏以病为由,要去清宴园里静养,老祖母想,清宴园里风景确实不错,兴许这小儿媳住上一段时间,心里的气消了,再叫小儿子去好生陪个不是,也就是了。少年夫妻老来陪,她和老头子也是磕磕碰碰的一辈子这么过来的,少人儿们总有些心气儿,可世间万事,敌不过如万岁月,等他们都知了世事,回头再看这些闹腾,怕他们自己也要羞呢。
因此到准了安氏的请,让人把清宴园给重新收拾了一下,安氏便搬了进去。
文玮失魂落魄的在外头游荡了几日,回来后,发现自己的院里竟是人去楼空,再一问,安氏搬去了清宴园里。她这是真打算如那天说的一样啊。知道了安氏的去向,文玮心里气苦,又倒生出些心安来,至少安氏没自请搬去家痷里,更没提什么和离的事情,他倒是狠狠的松了口气。
只是,松气之余,知道安氏并没真想和离,他倒是有力气生气了。他哪里懂得,安氏不提和离这件事,倒不是对他还有什么幻想,而是不愿意两边父母伤心,也不肯再折腾自己罢了。
文玮这一动气,想着你既心上没我,避而不见,我又何必再满心里都是你?世间女子多的是,我爱谁不行?我的真心你既瞧不见,我也不必再热心贴你的冷脸,何必为了你,苦了我自己。
他这也是白吃了一堑而未长一智,又拿出当初纳林姨娘进来的心思,再加上破罐子破摔的劲儿,干脆自许起风流来。倒是在山阳的风月界,留下了一段传奇。
他这边越来越没个约束,久了也就真习惯了这样的日子,安氏那边则是随着他越来越不成样子,不只死了心,更是干脆来了个视而不见,全当世上再没他这个人。
因此在这清宴里,竟是一住十多年。
从前祖母在世时,逢年过节的,安氏还能走出清宴园,在一大家子人面前露个脸,祖父母去世后,安氏竟是连清宴园的门都不出了。
而四叔后院里的妾室儿女,也是越来越多。
对这原本相爱的两个人,竟然闹成了这样,明明一个屋檐下,竟是老死不相往来般各自过着日子,一个美景相伴自得其乐,一个美人在怀风起水生,偏心里都有对方,长歌表示这两朵也堪称真爱界的奇葩了。
要说四叔自己不争气,四婶安氏也不是没有错,这两人之间,真是不好说什么对与错的话,都说相爱容易相守难,恋爱和过日子,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儿。
不过长辈们的恩怨情愁长歌也没本事去掺和,但看着安氏这么个大才女,就这么把在个园子里静静过着下半辈子,长歌觉得着实浪费。
她自有了要建女学的心思,就打起了安氏的主意来。
四婶这位难得一见的大美人儿,棋琴书画本就了得,原先闺中之时,已是扬州城有名的才女,十几年来日日浸淫其中,那可真不是寻常人能比的。
若是能把四婶拉出清宴园,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教教女学生,是不是四婶会过的更幸福些?
眼宽了,心就能宽。心宽了,和四叔之间,是不是还有机会峰回路转?
对于安氏,不管他和四叔之间还有没有和转的可能,长歌都真心希望她能幸福。
若这样出色明丽的女子,都无法过的幸福,实在是件让人心痛的事情。
她这边沉浸在四处美诗如画的风景之中,手中之笔,一点一点的描绘,并没有注意到,身后还站着个人。
真到感觉腰有些酸,口也有些渴了,长歌方从纸笔色彩的世界里出来,放下画笔,揉了揉手腕,对雪见叫道:“给我端杯温茶来。”
“你这画,很特别。”
听得声音,长歌转过脸去,见是李为庸,不由展颜一笑,道:“确实有些特别,这是油画,画具和颜料,原是番邦之物,是我四婶娘送我的。我家四婶精于书画,原是四婶娘家送来的东西,四婶因知道我别的不成,倒是绘画还能瞧,便送了我。我觉得有些意思,便试着学了段日子,和咱们大宋传统的画法很不同,我自己很喜欢。”
长歌瞧了不远处的天真一眼,见他正安静的躺在毡子上睡了,这才专心和李为庸说起话来。
寒喧了几句,长歌想着机会难得,刚好这会儿边上也没有人打扰,便对李为庸道:“这次特地让李表哥请李兄一道过来,是十一郎有事想请教李兄。”
李为庸眉头微动,心里却是好奇,文十一郎平时出门的时候并不多,和自己更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会有什么事情想着问他,并通过李文敬,特地请了他来呢?
难不成,文十一郎,是知道了她曾救过自己的事情?
“十一郎请讲。”
长歌组织了下语言,方正色道:“举凡世间流通,皆离不开物运,大宋南北物资调动,商品流通,甚至人口往来,又绕不过漕运。令尊乃漕帮之主,李兄对这物品流通,有何认识?”
“无物运,无流通,何谈经济?无经济,自无富甲繁荣。”李为庸沉思了片刻,应道。
这话,是真说到了点子上。
虽是浅而易懂的道理,可世间有多少浅显道理,无人总结,便不为人知的?
即便李为庸本为漕帮公子,长歌也不免多看了他一眼。
要知道有多少高官,也未必会对保证商品流通的物流运输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后世的人几乎人人都懂的道理,就是大宋官员,也晓得若无漕运,大宋南北交通受阻,就绝不会有如今大宋的经济繁荣,国力昌盛。
李为庸不过未及冠的少年,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值得长歌高眼一眼。
他有这样的认识,下面的事情也就好沟通了。
长歌笑道:“李兄见识果与常人不同。我亦深以为然。今日想请教李兄之事,正与此有关。”
便把自己想开一个物流公司,专业代理商家物品运输,兼管民间普通百姓信件往来的事情,与李为庸细细说了。
“……李兄觉得,我这构想,可能实现的可能?”
李为庸听的极是用心,见闻,却是一时也不好说什么,沉吟了一翻,方道:“十一郎想常人之不敢想,要说这件事情的意义,实是利万民,利国家之好事,至于是否可行,我倒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实在是,这绝不只是十一郎自己的事情,还涉及税赋和官府路政。想做成,绝非易事。只是,世间万事,若未开始便断言不成,或是看到难处就放弃,怎知真的就不成?我回去后,再做了解,过些日子,再回答十一郎,可行?”
长歌笑道:“这是自然。”
“不知十一郎,怎生出这样的想法来的?”
这文有十一郎,不过才十三岁罢了。所想之事,竟是前无古人。其实说要起她口中的物流,自古以来便有,如官府的递铺驿站,便附带着物流的职能,且一般驻军,亦有传送物资的任务,只那都是官方所为,民间行商,多是靠自己自力更生,所用的,也是自己的人,实在自己无法运输的,也会雇用车马行,又为安全者,亦会请镖局相帮。只是这专以物资运输当成生意来做的,还真是没有。
且正如他刚才所言,大宋税赋之中,有行商税,商品经各个行政地,都是要交过路税城门税的,十一郎要做的运输生意,税赋这一块,先就绕不过去,这税,是算在运送费用之中,还是由商家自出?而这税收一事,虽大宋有统一规定,然各州府收际收取时,则也有不同。这和商家首先就扯不清楚了。若是商家有人跟着,还好计较,可听十一郎才刚所说的话,刚是根本没有让商家插手的打算,商家交付货物,她全权负责送到目的地,其中若有任何差池,责任都是她想自担的。
另外,除了这税赋,还有护送的押运队伍过各州府的路引,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所以他才说,做成这样的一件事情,离不了官府的支持。
倘若哪一级行政区扣押物品,所送货物无法及时送到,这样的责任,可还真不是轻易能承担得起的。偏偏这样的事情,绝对会发生,而且是会时常发生。
很难保证路引不出任何问题。因为这不是一次性就能办好的,需要路经各地时,当场办理过境手续。
长歌笑道:“我从小就希望有一日,能踏遍大宋河山,看遍天下美景,再加上我外祖家经营着大宋最大的商行,从前常听喜来登的实际掌舵人,我外祖家的八姑祖母老将军夫人提起这货物流通的事情,慢慢的,心里倒有了这样的想法。这几年因我的腿疾,整天只能待在后院之中,想的难免就多了些。李兄问我怎么会想到这件事情的,我还真是说不上来,或许这样的想法,也是顺其自然吧。只是越细想,越觉得这是件万利之事,便动了想做成功的心思,听李表哥提到漕帮公子是他的好友,这才起了结交之心。漕帮虽非官方组织,可在漕运之中,却有着任何官方机构都无法取代的作用,若是能认识李兄,或许我的这个想法,还真有实现的可能。只是不知道李兄对这件事情,有没有兴趣罢了。不过,不管李兄有没有兴趣,我总得先问问才是。哪怕不能与李兄合作,能听取听取李兄的意见,也是大幸之事。”
李为庸看着长歌,一时竟不知作何感想了。
他十三岁的时候,可曾有这样的宏想伟志?
兴天下商品流通,哪怕是户部或者三司的高官们,可曾敢这样想过?又或者,想过,但却绝没有想到这样的办法,自己做一个专门负责货物流通,信件往来的运行?
一时之间,李为庸竟也有些热血沸腾,想一并做些什么的感觉。
漕帮,不过是底层的那些船夫,走卒,运工的自发组织,因大宋国力无法单靠官府军队运送这一年数百万担的税粮,这才不得不依托民间的力量,而衍生出来的组织,靠的,不过是官府的漕运体系罢了。
漕帮帮主,虽无官职,但其权力任何人都不敢小觑,可李为庸知道,即便他将来代替父亲,成为漕帮之主,手中掌握了让官府都不敢小瞧的权力,但这一切,都非是他李为庸自己的本事。
更何况,想得到漕帮帮众的认可,取得帮主之位,也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假如这文十一郎真有这样的豪志,并且真的去做了,是不是也会成他的助力?同这样的一个商行合作,对他在漕帮地位的稳定,有着绝大的好处。可,一个只能坐在轮椅上的十三岁少年,他凭什么相信,文十一郎,不是一时兴趣,满口胡言?他实在看不到,这件困难天高的事情,他有做成的希望。
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能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本身,是不是就很不可思议?他为什么不能相信,文十一郎可以做到?
想到这里,李为庸笑道:“十一郎的提议,我确实心动,若是可行,我自是愿意与十一郎合作的。如果十一郎真打算做,又想从哪里着手开始?”
这便有考较的意思了。
这物流公司的事情,长歌不知道考虑了多长时间,所能遇到的实现困难,该怎么开始,方方面面,她能想到的,都去想了,不只想,还一笔一画,但凡自己想到的,都做了记录。因此李为庸开问,长歌便答道:“虽说志在四方,流通天下,只凡事都不可能一跌而就,从小处做起,慢慢积累经验,站稳了,再开始迈步,才能尽最大的可能保证少走弯路,少遇失败。以我们现在的经验和财力物力,想一开始便做大,输通举国南北之路,显是不可能的,我若真说这样的话,李兄怕是从此再不会理会我,只当我是个纸上谈兵之徒了。我想,开始之时,不如从某一路开始,山阳及是南北交汇之地,又有全国最大的盐场,只盐商就有不少,何不必做一路的运输起步?做的好了,有了名气,商为即便为减少运输成本,也会来找我们运行。而这,不只能打出名头,又可以积累经验,到时候一步一步,把运行的生意,推向全国。至于路税路引,则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与托运方,一一商议,虽复杂些,却不是不能做的。”
听得这一席话,李为庸方信自己的判断果然没有错,这文十一郎确实不是信口胡说,而是真的对事情的可行性作了很好的规划。
但是让他现在就表示想合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再说长歌如今只说请教,可没正式提什么合作的事情。
而他,也需要回去再仔细想想。
事情虽是文十一郎提出,但要想实施起来,仅凭他一个十三岁的小郎君,且这小郎君还是个假郎君,又行动不便,只能坐在椅子上,怕离了他的支持,还真不行。
而物运,整个大宋国,谁人又敢说,比漕帮更知道其中的内情门道了?
若有他的参与,虽困难依旧存在,却能做到事半功倍。要知道漕帮虽是民间组织,却是和负责漕粮入京的官府部门,相依相存的关系。关于运输的一应手续,再没有比漕帮更知道如何花最少的时间,以最小的代价来解决的了。
文十一郎能想得到找他来询问,还真不是个笨人。
毕竟大家都是少年人,彼此之间也好说话,哪怕他真个什么也不懂,听了十一郎的构想,顶多也只会当文十一郎在开玩笑或者做梦罢了。可若文十一郎拿这样的事情去问他父亲,现任漕帮帮主,以她的年纪,哪所父亲觉得这件事情确实大有可为,可也绝对不会去相信一个十三岁连自己都无法象正常人一样行走的少年,能做出这样的大事来。除了付之一笑,更甚者,骂他一句异想天开外,再不会去理会的。